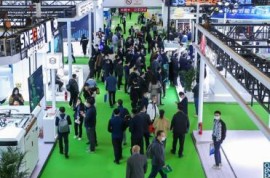过去十年,清洁能源发展速度超乎预期,为应对气候变化、刺激经济增长、保障能源安全,提供了复合型解决方案。清洁能源、能效提升和绿色电力推广,成为引领全球能源转型的中坚力量,推动全球能源体系发生根本性变化。面对能源转型重塑地缘格局带来的契机与挑战,中国作为最大的清洁能源生产国,应发挥自身结构性优势,推动灵活多元的清洁能源外交,促进建构更加公平合理、包容共享、绿色安全的国际能源治理新秩序。
河北省平山县岗南镇李家庄村附近荒山上的光伏发电站 杨世尧 / 摄
全球绿色复苏三大特征
新冠肺炎疫情造成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萎缩,为了应对这一冲击,各国政府积极制定经济复苏政策。然而,传统的依赖化石能源消耗的经济刺激,可能加剧不可逆转的气候变化和其他环境与健康风险。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IRENA)总干事弗朗西斯科·拉卡默拉指出,各国政府在制定后疫情时代经济刺激和产业复苏方案的过程中,需要融入清洁发展理念,加速向可持续性的脱碳经济体和富有弹性的包容性社会转变。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呼吁各国利用疫情后经济复苏的机会,携手采取变革性绿色复苏举措,促进高质量绿色发展,构建更加清洁、公平、安全的世界。全球绿色复苏态势存在以下三个特点:
一是全球绿色复苏与碳中和目标紧密结合,成为新的大国共识。目前,包括中美欧在内的127个国家和地区,作出到21世纪中叶实现碳中和的重大承诺,支持绿色复苏,控制全球升温速度。2020年5月,欧盟公布总值达7500亿欧元的复苏计划,推出一系列支持绿色转型的措施,将落实《欧洲绿色协议》和《欧洲工业战略》作为后疫情时代欧盟“化危为机、复苏经济的绿色动力”。2020年9月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上,习近平主席倡议各国推动疫情后世界经济“绿色复苏”,汇聚起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合力。中国力争于2030年前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美国拜登政府宣布重返《巴黎协定》后,将绿色经济复兴作为气候政策的重心,重点关注与气候相关的产业结构、市场需求、基础设施投资、关键资源等,从而确保美国在2050年之前实现100%的清洁能源经济和净零排放。继2015年《巴黎协定》签署和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出后,推动全球绿色复苏的大国共识,成为加速全球能源转型的重要引擎。
二是全球绿色复苏中强调能源转型的公平过渡和弹性适应。欧盟在绿色复苏中形成新的《公平过渡机制》,提议筹集1000亿欧元,以确保碳密集地区在进行工业和经济转型升级时实现“公平过渡”,并帮助疫情严重地区朝气候中立目标发展转型。拜登政府致力于将美国建设成为“气候弹性和环境正义国家”:对清洁社区、建筑节能、弹性的基础设施建设进行开创性投资,制定气候适应议程;注重少数族裔、低收入群体与工人的环境气候权益。但是,欧美的“公平过渡”多局限于国内/地区内能源正义,忽视了全球能源转型中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气候适应能力提升、能源可获性和公正转型诉求。
三是绿色复苏中能源转型与数字化转型的耦合度不断提升。2019年,IRENA和国际能源署就提出了“智慧能源新业态”的理念,倡导加快能源与现代信息产业的融合发展,推进电力网、互联网、通信网、光电网的多网融合互通,形成高效配置的智能化平台。2020年3月,欧盟出台《欧洲工业战略》,明确提出绿色和数字双重转型理念,强调随着波动性和分布式清洁能源占比的增加,数字化技术在保持电网稳定方面发挥的作用将更加关键。2020年12月,欧盟颁布《全球变局下的欧美新议程》,强调欧美需要通过绿色技术联盟来领导可再生能源、电网储能、电池、清洁氢以及碳捕获等市场,通过对绿色技术、贸易和标准的主导来强化欧美绿色数字双重转型。
能源转型重塑地缘格局
以石油、煤炭为代表的传统化石能源生产链,都同特定的地理位置密不可分。与之相比,可再生能源具有资源分布的广谱性和生产的连续性等特点,其供给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风机、太阳能光板、储能入网、绿色制氢等技术的革新。能源转型正对全球地缘格局产生复杂而深远的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重塑全球权力分配、国家间关系及地缘政治冲突。
英国拟 2030 年禁售汽柴油车,图为伦敦一辆正在充电的电动汽车
第一,国际体系中的国家被“再定位”且领导性资源发生变化。国家能源转型的成本,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化石能源的依赖程度、国内清洁能源发展及其商业化水平。能源生产与分配的话语权正由资源国向资源与技术国家共同掌握转变,未来甚至可能向技术国家倾斜。过去对地缘政治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化石能源出口国呈现出脆弱性,若不在新的能源时代调整经济结构,其全球影响力将逐渐减弱。西方国家掌控的清洁能源知识产权与技术产业链,使其在能源转型中仍具优势,且可能进一步加剧南北差距,并恶化全球范围内的能源正义问题。
第二,能源外交格局与国家间结盟态势加速变化。伴随着全球化石能源需求的下降,相关集团组织可能会松散瓦解。相反,基于能源转型和清洁能源发展需要,能源外交出现绿色化转向,各种新的国际合作机制、伙伴关系、政策网络不断涌现。西方清洁能源先驱国家(德国、荷兰、丹麦、西班牙、美国等),在推进能源外交格局转型初期发挥了不可小觑的作用。如德国因不满国际能源署对化石能源的重视,于2004年推动了国际清洁能源大会(IRECS)、21世纪可再生能源政策网络(REN21),2009年主导建构了IRENA。美国先后推进了亚太清洁发展与气候伙伴关系(APP)、全球性清洁能源部长峰会(CEM)等机制的发展。这种外交转型态势不限于西方国家,如2015年巴黎气候变化峰会上,印度宣布成立国际太阳能联盟(ISA),倡导热带地区国家加入,以此提升自身在太阳能领域的全球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
第三,绿色贸易和绿色金融新格局中的“共同治理”与“规则博弈”并存。一方面,清洁能源发展与电网互联密不可分,增加绿电交易量的同时,增强了电网的抗波动性和稳定性。太阳能和风能等波动性可再生能源,需要灵活互联的跨区域、跨国乃至跨洲的电力系统实时调峰网络。这种跨境电力交易需要电力在管理良好和透明的市场中自由流动,也为区域合作带来新的机遇,如IRENA的非洲清洁能源走廊(CEC)倡议被纳入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非洲基础设施发展计划,旨在促进绿色能源市场的跨境电力贸易,并推进非洲各国的绿色融通与公平性低碳转型。
另一方面,以绿色产业为重心的国际新经贸结构,逐渐成为未来支撑世界经济的主流,与清洁能源技术相关的贸易争端数量也有所增加。目前,世贸组织还未能解决清洁能源产品贸易因各国关税、差别性补贴和不一致的技术标准所产生的阻碍问题,清洁能源的全球推广、公平贸易和协调治理能力亟待加强,须寻求异于化石能源的国际治理架构。同时,随着经济贸易和金融投资格局的绿色转向,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和新兴发展中大国都已加大对绿色技术的研发投入。围绕着绿色能源技术及知识产权、绿色供应链、碳金融市场、低碳法律配套等领域而进行的国际规则和标准博弈将日趋激烈。
塑造清洁能源时代的外交优势
国际能源权力结构的变化,往往是国际体系重大结构性变迁的前提和条件,如英国和美国的霸权维系分别离不开来自煤炭和石油的能源支持。作为下一代能源体系的主导因素,清洁能源将在国际体系主导权争夺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一国在能源转型中的外交战略优势,有助于其在全球治理新秩序建构中发挥关键作用。中国自2009年超过德国和美国成为全球清洁能源生产首位大国,拥有绿色能源供给侧的结构性优势,为清洁能源外交的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清洁能源外交的核心,是基于利益共享的原则,以绿色共赢的理念,推动构建灵活多样的新型大国关系,并通过供应清洁能源的地区公共产品,提升中国外交布局中的绿色资源性权力,丰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含义。
我国应把握清洁能源发展中的优势,建立可持续的新型能源大国关系。可以就某个清洁能源合作议题建立制度化、常态化的沟通和协调机制,或将清洁能源议题同其他政治经济议题进行良性互动联系,借助其他平台为大国磋商协调提供空间。同时,可以在“一带一路”沿线清洁能源项目上,同其他大国开展第三方合作,探索建立大国清洁能源合作示范区,扩大合作共赢空间。在这一过程中,要注重中国实践与国际能源标准和机制对接,同时通过清洁能源合作和最优实践推介来推广中国标准。
可大力拓展基于清洁能源的“绿色南南合作”模式,推进绿色能源国际机制创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生态脆弱和气候适应能力低的发展中国家,未充分开发清洁能源资源。而沿线大部分国家提出碳中和和清洁能源发展目标,为国际清洁能源合作提供了契机。中国应立足于既有的区域和国际多边机制,加强“APEC可持续能源中心”“东亚峰会清洁能源论坛”和“中国—东盟清洁能源能力建设计划”等区域合作机制的协调,针对某一清洁能源领域推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长效性合作机制。同时,可以建构基于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和社会部门共同参与的包容性清洁能源政策倡议网络,大力推进以城市为载体的清洁能源合作伙伴网络构建,实现四两拨千斤式的多轨外交实践。